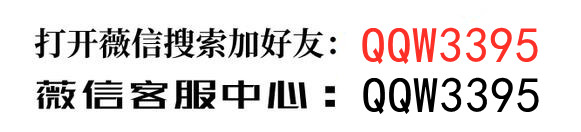1866年7月,《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短篇小说《乔治·戴德洛案》。时至今日,人们还记得它是对“幻肢”疼痛的早期生动描述:叙述者戴德娄在内战中失去了双臂和双腿,但他失去的四肢却感到紧绷和灼烧,无法安抚。
“我的左手开始感到最剧烈的疼痛,尤其是小指;这些缺失部分真实存在的想法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我有时很难相信它们不存在,”戴德洛回忆道。“夜里,我常常用一只失去的手去摸索另一只。”
尽管自1861年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第一次炮击以来,美国人已经读过很多战争故事,但《乔治·戴德罗》让公众注意到退伍军人带回家后改变了的身体和思想。许多读者误以为这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捐款源源不断地涌向故事发生的美国陆军神经系统损伤和疾病医院(也被称为“斯顿普医院”)。有些人来到医院,希望能见到戴德洛本人,但当院长告诉他们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时,他们感到很失望。这篇文章的作者几十年来一直不为人知。
从数字上看,内战是一场医疗灾难,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创伤、感染和传染病,医生们无力阻止。新型前置装填步枪和被称为“米尼球”的子弹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更精确地射击——这对将军来说是福音,但对士兵和外科医生来说却是诅咒。圆锥形和空心的米尼球在飞行中旋转,然后在撞击中变平,粉碎骨头,撕裂身体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试图将某人缝合在一起是没有希望的,尤其是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的情况下。
外科医生通过完善快速截肢术,采取了他们唯一能采取的方法。在今天,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内切除肢体听起来很野蛮,但速度是他们对抗失血、感染和疼痛的唯一武器。历史学家估计,到战争结束时,外科医生已经切除了大约3万个肢体。

其中一位外科医生塞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被神经损伤的病例所吸引,他的同事们认为这些病例无法治疗。当他在费城的专科病房人满为患时,陆军医疗部门创建了一家专门治疗神经疾病的医院。士兵们涌向特纳巷医院,寻求缓解伤口愈合后持续存在的疼痛。米切尔描述说,一名男子因神经损伤而“神经紧张、歇斯底里”,以至于他的家人“认为他有部分精神失常”。
《乔治·戴德洛案》是根据米切尔在特纳巷的经历写成的。它反映了无数被截肢的士兵的证词,他们都描述了同样的感觉,那种失去的胳膊或腿还在的感觉,有时无害,有时却很痛苦。在匿名发表了戴德洛的故事后,米切尔把他的临床材料变成了医学杂志和书籍的文章,包括1872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神经损伤及其后果》。他以“现代美国神经学之父”的身份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这是基于内战后挥之不去的幽灵般的痛苦。
米切尔并没有发现这种被他命名为“幻肢”的现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外科医生认为它“值得惊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医生往往会忽视那些没有明显生理原因的病人。一条不存在的腿怎么会剧烈抽筋呢?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寻找客观证据,当没有证据出现时,他们开始怀疑有人口是心非。“装病”,也就是为了逃避服兵役而装病,是米切尔的一大心病,但他相信,特纳巷医院的大多数病人并不是装病。然而,“无损伤疼痛”的可能性挑战了当时科学医学的基本前提。

当然,在米切尔1871年创造这个词之前,内战老兵就已经很清楚幻肢综合症了。它在截肢者中普遍存在,尽管由于医生的怀疑,他们有时不愿谈论它。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堡在米切尔的记录中发现了这些老兵的情绪。“当然,”Henry S. Huidekoper解释说,“和其他失去肢体的人一样,手指的感觉很明显,而且手指的各个部位经常感到疼痛。”
伊利诺伊州贝尔维尔的亨利·a·基尔彻(Henry A. Kircher)也认为幻肢的疼痛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疼,”他说。米切尔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对这些病人进行了随访,寻找他们持续症状的详细信息。一名住在肯塔基州的男子描述了他被截肢的脚上持续的灼烧感。不过,他不敢浪费钱去看当地的医生,除非著名的S.威尔·米切尔能给他提供一封信,证实他的疼痛是真的。
米切尔的病人Henry S. Huidekoper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失去了右手,他经常在梦中开始疼痛。“我经常在梦中写作,”他在1906年说,那只手被截肢40多年后。“我试图用肌腱来控制和引导笔。”写字的手,似乎恢复了,拒绝合作。相反,肌腱恶意地抽筋,“因为疼痛把我从最深沉的睡眠中惊醒。”

除了努力寻找治疗疼痛的方法外,退伍军人还必须适应削弱了他们自我意识的残疾。小说中的戴德洛失去了四肢,感觉“对自己、对自己的存在越来越没有意识……我想不断地问别人我是不是乔治·戴德洛。”在这里,他的故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一个朋友说服他参加一个灵媒的聚会,灵媒会召唤他被截肢的腿上的鬼魂——字面上的幻肢。在沉入地面之前,他在物化的腿上短暂地行走。这次奇怪的相遇给了戴德洛希望,在死亡中,他将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与他分散的部分重聚。
米切尔的意思可能是这个夸张的结局是对唯心论的讽刺,怀疑论者指责唯心论运动在内战后剥削了极度悲伤的家庭。但这也微妙地承认了医生的无助。戴德罗求助于唯心论暗示了一种米切尔和他的医学同事无法解决的情感需求:在创伤性损失后感觉完整的需求。
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失踪的肢体重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63年的《医院素描》(Hospital Sketches)中,一名受伤的士兵设想,“我的腿将不得不从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出发,我的手臂将从这里出发……与我的身体相遇,无论它在哪里”。这些想象中的团聚也是修复这个分裂国家的一个隐喻。
尽管米切尔在特纳巷帮助了许多病人,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尝试治疗幻肢痛,包括电刺激和再次截肢,但收效甚微。作为一名医生,他把希望寄托在最终找到一种他可以治疗的物理损伤上,这是造成幻肢的物质原因,而他的病人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的身体和思想受到困扰,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为您推荐:
- 1分钟学会“中至麻将开挂!详细开挂教程已更新-知乎 2024-10-31
- 德国在友谊赛中以4比1击败日本,加剧了2024年欧洲杯主办国的危机 2024-10-31
- 最新教你“奇迹麻将开挂神器下载”其实确实有挂 2024-10-31
- 1分钟学会“新九哥大厅开挂!详细开挂教程已更新-知乎 2024-10-31
- Armin van Buuren带领阵容首次亮相迪拜音乐节 2024-10-31
- 1分钟学会“中至万年麻将开挂!详细开挂教程已更新-知乎_足球_体育_喜临门 2024-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