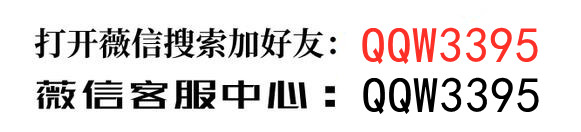上世纪80年代,位于伦敦东南部的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从一个破旧的工业荒地变成了一个银白色塔楼林立的半岛,这些塔楼高得足以顶到云层。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时代保守主义的承诺,写在玻璃和混凝土上:拆毁旧的,解放新的,释放自由市场,促进繁荣和生产力。
今天,金丝雀码头依然熠熠生辉,依然富有。但它也是没有灵魂的。宽阔、空旷的街道贯穿于塔楼之间,没有伦敦老街区那种随意、有机的繁荣。上周,在泰晤士河对岸的会议中心——伦敦杂志(Magazine London)举行的首届ARC论坛上,与会代表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个缩写是负责任公民联盟的缩写,这是一个由政治家、思想家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国际组织,他们“不相信人类必然和不可避免地徘徊在世界末日灾难的边缘”。这一声明可能反映了一个致力于寻找令人振奋的未来愿景的聚会,也可能是否认气候变化的暗号。坚持这种模棱两可。
对冲基金经理保罗·马歇尔爵士(Sir Paul Marshall)是ARC的支持者之一,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可以与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匹敌的媒体影响力机器,但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和阻力。马歇尔控制着一个英国有线新闻频道和一本杂志,可能很快还会有一份报纸。但他的帝国在两种冲动之间摇摆不定——大西洋两岸的保守主义也是如此。就像共和党中的一些人一样,马歇尔帝国——以及arc——希望与良心资本主义和道德生活联系在一起。然而,获得右翼关注的最快途径是通过抱怨、低级笑话和阴谋论。
海伦·刘易斯:没人应该关心女人的“死亡人数”
ARC的另外两位公众人物是来自支持英国脱欧的智库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的菲利帕·斯特劳德(Philippa Stroud)和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斯特鲁德男爵夫人主持了几次会议,戴着珍珠项链、珍珠发带和珍珠耳环,看起来很贵族,而彼得森则穿着他最荒谬的个性化西装,其中一套让他看起来像《蝙蝠侠》中的双面人。斯特劳德和彼得森巧妙地体现了这种困境:现代保守主义是更真诚地依恋家庭、信仰和国旗,还是哀叹算法“不清醒”?见鬼,彼得森一个人就代表了组织。在报道彼得森五年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类彼得森的粉丝:喜欢他的书的人,以及喜欢他的社交媒体帖子的人。这些书是带有神秘主义和哲学色彩的自助书籍。这些帖子的内容包括“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都归咎于错误的教育”和“永远不要购买带有智能速度辅助的车辆”。
在会议上,彼得森以电视布道家的节奏滔滔不绝地谈论责任和希望。与此同时,他的YouTube频道发布了一首“后现代主义饮酒歌”,他在其中模仿歌词,其中包括“米歇尔·福柯是一个真正的变态/这让他非常悲伤。”(说真的,看。社交媒体的收获就是音乐剧的损失。)会议中最受欢迎的两个视频之一是一个快乐文化战士的演讲,攻击格蕾塔·桑伯格,赞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另一个是关于西方文明的哲学基础的四方讨论。
根据新闻材料,ARC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对更美好世界的愿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公民都能繁荣、贡献和繁荣,并能找到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办法。”我试着去理解这个善意的笨蛋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ARC主办了两个平行的会议。其中一个是认真的、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许多人受到深刻的个人信仰的驱使,与贫困、社会流动性和不公正作斗争。另一个则是互联网上流行的对“觉醒思维病毒”的末日谴责。但是,除了对现代文化感到不安之外,这些群体还有什么共同点吗?如果没有,那是谁在剥削对方?
在会议的第一天,保罗·马歇尔(Paul Marshall)指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扶贫工具”,但它已经被任人唯亲所腐蚀,不尊重人的尊严。他认为,它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因为年轻一代没有体验到它的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它为ARC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我们试图做的不是边缘文化辩论,”会议组织者约翰尼·帕特森(Johnny Patterson)告诉我。“它实际上是真正的肉。”他想解决诸如“我们如何应对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对我们机构的信任崩溃?”
考虑到这个崇高的目标,阵容似乎,我们应该说,不拘一格。帕特森也承认这一点。他告诉我:“我不认为我们会在很多会议上看到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一位英国保守党的资深政治家——“后面跟着鸭子王朝的团队。”“在某种程度上,这表明人们希望认真对待政治,但我们认识到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可避免地,我不断将ARC与今年早些时候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全国保守主义会议(National conservative Conference)进行比较,在那次会议上,毫无吸引力的民粹主义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出生率问题。那次活动感觉像是反建制右翼分子的集体治疗,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英国脱欧、一个强硬的保守党政府——但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仍然不开心。
总的来说,ARC的活动没有NatCon那么古怪。坦率地说,它的资金更充裕,也更专业。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可卡因是上帝告诉你钱太多的一种方式?错了!真正的奢侈是让威利·罗伯逊(Willie and Korie Robertson)夫妇飞到伦敦接受20分钟的采访,尽管在英国没有人看过《鸭子王朝》。他们必须先给观众看一段视频,解释这是一个真人秀节目,关于大胡子的人制作卡祖笛。
NatCon和ARC都有国际野心:前者是以色列作家约拉姆·哈扎尼(Yoram Hazony)的创意,而ARC会议则有很多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参加。在我看来,这个全球网络的主要影响是突显了美国中右翼曾经存在的巨大空白。在ARC会议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来自其他英语国家的具有实际执政经验的温和保守派的讲话。然后美国的贡献就像穆罕默德·奥兹或维韦克·拉马斯瓦米。
海伦·刘易斯:为什么这么多保守派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许多发言者提到了他们的个人信仰,或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的重要性。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曾在最近几任保守党首相的内阁中担任过大臣,他知道如何取悦听众。他在一次关于工作场所多元化项目和房地产市场金融化问题的演讲结束时声称,ARC展示了欣赏“雅典和耶路撒冷给我们的东西”的必要性——不,不是美味的葡萄叶,而是普罗米修斯(prome修斯)和犹太教精神的混合体。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从众神那里获得火焰,尤其是犹太教的精神,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平等。”这有意义吗?不是真的。听起来深沉吗?噢,是的。观众们都很喜欢。
ARC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纠葛是与会者希望重新审视过去伟大的神学分歧:在一次休息时,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圣奥古斯丁当然赞成多纳图派重返教会。”当然!在第二天的演讲中,美国天主教主教罗伯特·巴伦(Robert Barron)讲述了中世纪神学家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之间关于上帝是否会犯罪的争论。“我要站在前面,”他说,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辛辣口吻。"阿奎那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我身边的一个人开始大声鼓掌。这是为那些对尼各马可伦理有强烈想法的人准备的达沃斯论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方便的名字来形容马歇尔、斯特劳德和彼得森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交集——基本上是好撒玛利亚人,但极度在线。不过,也许它不能被命名,因为它缺乏内部连贯性。谁会认为《登山宝训》中加入一些关于格蕾塔·桑伯格的低级笑话会更好呢?
然而,我要赞扬ARC揭露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断层线。一系列关于能源的讨论试图应对减少碳排放的挑战,同时微妙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许多美国右翼人士甚至不愿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大问题。
分歧的另一个来源是机构的角色——曾经被保守派所喜爱,现在更多的是被视为秘密进步主义的载体,或者只是纯粹的骗子。“央行官员是一群罪犯,”经济学家查尔斯?盖夫(Charles Gave)在一片欢呼声中说。即使是普通的企业也受到了一些抨击。戈夫谈到了享有特权的老板们现在是如何与“怨恨产业”——我猜他指的是基于身份的民权运动——沆瀣一气,以维护自己的权力。这是自由主义者抱怨右翼煽动枪支和堕胎的文化战争,以使工人阶级投票反对其经济利益的一个巧妙的翻转。
曾经乐于成为建制派的保守派,现在谴责这个被大型科技公司、银行、“深层政府”、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个人以及拥有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项目的行善公司操纵的体系。一个关于良好治理的小组讨论变成了一场加密货币的恋爱,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介入并提出案件的另一面。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位梳着男式发髻、穿着乐福鞋、不穿袜子的小组成员说,比特币“就像黄金和互联网生了个孩子”。这显然是一件好事。
我非常喜欢“富人反对资本主义”之类的东西。但我看不出保罗·马歇尔对新西奥多·罗斯福的呼吁——“一个准备承担既得利益的人,以摆脱商界的裙带关系、监管束缚和虚假美德”——是否会被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或彼得森(Peterson)所接受,凯文·麦卡锡是被罢免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他向ARC发送了一段视频演讲,或者彼得森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资本主义不应该为你的失败负责”的演讲。或者,实际上,是那些在马歇尔的GB新闻频道上抱怨“沃克马”的空洞的挑衅者。
交易似乎是你容忍马戏表演和文化战士来吸引人们的注意,然后很快!——一旦你让他们上钩,就对监管俘获提出冷静的批评。我不能嘲笑这一点,因为新闻业也这样做,但我确实质疑它对现代保守运动的作用。许多人狼吞虎咽地吃下美味的食物,把蔬菜推到一边。
关于这一点,在主厅讨论超越的间隙,我躲进了休息空间,在那里我不断发现知识分子暗网的中坚分子——一群在2010年代末因挑战各种左翼正统观念而在互联网上出名的人物。反对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活动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已经登上了舞台,但其他人在外围徘徊,与人握手并接受采访。这是埃里克·温斯坦(Eric Weinstein)与英国喜剧演员吉米·卡尔(Jimmy Carr)的谈话,他是创造了“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一词的grience griess。埃里克的哥哥布雷特(Bret)是一名生物学家,他在2017年失去了一所大学的工作,现在在X(以前是Twitter)上沉思,说“内塔尼亚胡是哈马斯危机中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不要问。)在ARC的最后一晚,在拥有2万个座位的O2体育馆,知识分子暗网的忠实拥护者彼得森将右翼评论员本·夏皮罗(Ben Shapiro)请上了台。旧势力又重新集结起来,比他们刚出道时更加保守——在某些情况下,更加阴谋论。
海伦·刘易斯:互联网喜欢嗜极生物
我去和反觉醒战士詹姆斯·林赛打了个招呼;上次我们谈话时,他呼吁以战争罪审判新冠病毒科学家并处以绞刑。他似乎比一个刚刚逃离一个饱受战争罪行折磨的国家的人要快乐得多,他证实自己不是在说话,只是在随车。我一直在想,在过去五年的政治冲击中,知识分子的暗网是否还保持着联系——2019冠状病毒病(covid -19)、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活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答案就在这里。我想,彼得森还记得他的老朋友,这是一种善良的表现,明智的做法是不让更多的老朋友出现在镜头前。
参加这次会议的每个人都会同意这样的诊断:现代世界是孤独的、原子化的、颓废的。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失败的地方。难怪保守运动一直盯着它的敌人:抱怨“圣格蕾塔”要比告诉化石燃料公司他们只能赚大钱而不能赚大钱容易得多。保守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好事。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女性不想呆在家里照顾孩子,因为这会影响她们的职业生涯,而那些只为了最大化股东价值而存在的公司也不会帮助她们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啊,如果加密货币是答案,那么问题就不是“我们如何防止另一场银行业危机?”而是“我怎么能在舒适的家里失去毕生的积蓄呢?”
离开ARC时,我并没有感到绝望,只是感到失望。保守主义需要在会议的表面下进行斗争。它还需要开始表现得像一场运动,能够建立制度,而不仅仅是摧毁它们。然而,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在严肃和杂耍之间做出选择。右派需要与自己进行一些争论,它需要确保最优秀的人获胜。
为您推荐:
- 3分钟带你了解情怀宜春麻将外卦软件!详细开挂教程已更新-知乎 2024-10-22
- 3分钟带你了解闲逸斗地主有没有挂(详细真的有挂)-知乎 2024-10-22
- 欧尼熊——网络热梗背后的神秘人物,你了解多少? 2024-10-22
- 教学教程“微乐内蒙古麻将推倒胡挂下载!详细开挂教程已更新-知乎 2024-10-22
- 玩家必学“牵手跑得快游戏软件挂怎么卖(详细真的有挂)-知乎 2024-10-22
- 新X用户每年只需支付1美元就可以在该平台上发帖 2024-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