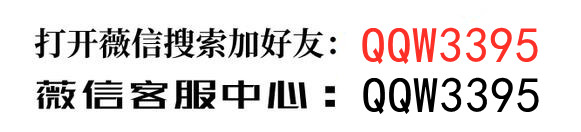在她工作的第一天,这位年轻的生物工程专业学生爬下加州伯克利一家癌症实验室地下室的台阶,看到有人在斩首一只老鼠。
学生伊丽莎白·瓦吉斯(Elizabeth Vargis)感到头晕。她抓住一把椅子。作为一个印度移民的孩子,她的成绩下降,刚刚让她失去了奖学金,她认为,她难以保持直立也意味着她的研究生涯的结束。
几天后,她的新上司沙马拉·戈帕兰·哈里斯(Shyamala Gopalan Harris)听到她的学生自责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科学家,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你那天吃东西了吗?”
年轻的生物学家没有。
“你必须吃东西!”
他的回答并不热情——更多的是“你傻吗?”而不是“我很遗憾你晕倒了,”瓦吉斯说。它也不像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的警句那样现成,比如在她女儿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竞选总统期间,关于椰子树的警句在网上引起了选民的想象。
但在教授的告诫中,瓦吉斯听到了她自己的印度姑姑的回音,并肯定了她属于一个科学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她和她的教授都从未完全感到自在。
“她想让我待在那个房间里,”瓦尔吉斯说。她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在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经营着一个实验室,她把自己的事业部分归功于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她想给每个人一个机会,一个平等的机会。”
在那次邂逅的六年后,戈帕兰·哈里斯于2009年死于癌症。今年秋天,她可能成为女儿竞选传记中最知名的人物。在演讲中,哈里斯经常提到对她影响最大的那个人:那个“有口音的棕色皮肤女人”,她19岁离开印度,抛弃传统,嫁给了一个牙买加人,在美国定居下来。
但根据对20多位戈帕兰·哈里斯共事过、指导过或结识过的人的采访,副总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往往忽略了她母亲在她选择的国家对种族主义和厌女症更为反抗的态度。她性格的这一部分不仅体现在她参加的争取黑人权利和结束越南战争的斗争中,也体现在她领导的乳腺癌实验室中。这个实验室是科学界的一个小角落,由白人男性组成,在她看来,经常对像她这样的人不友好。
Shyamala Gopalan的叛乱很早就开始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她就读的印度高中,女孩坐在教室的一边,男孩坐在另一边。越界可能是危险的:最好是成群结队地接近异性。
“这可以保护你免受关于你和某人谈恋爱的谣言的影响,”同学r·拉贾拉曼(R. Rajaraman)说。
戈帕兰没有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大女儿,她来自一个享有特权的泰米尔婆罗门家庭,她对男孩们说话毫不羞愧。

19岁时,戈帕兰告诉父亲,她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营养科学研究生课程录取了。拿着1600美元的奖学金,她于1958年前往伯克利。
戈帕兰只能靠自己了。她的家人在伯克利没有联系人。
“她很孤独,她说这很艰难,”她的老朋友和合作者朱迪思·特金(Judith Turgeon)说。“但她坚持了下去。”
在伯克利激进政治的坩埚中,戈帕兰找到了亲密的朋友,其中许多是黑人。她加入了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学习小组,该小组的成员最终帮助建立了黑豹党。尽管她出身于上流社会,但她在人群聚集的地方都很自在,即使是在西奥克兰的黑人区,同学们说那里往往会让其他外来者感到不安。
戈帕兰本来是要回到印度包办婚姻的。但在1962年秋天,她遇到了唐纳德·哈里斯(Donald Harris),一个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牙买加人,他也加入了伯克利的黑人研究小组。第二年他们结婚了。

他在学术上步步高升;她在侧身移动。但沙马拉·戈帕兰·哈里斯(Shyamala Gopalan Harris)坚持自己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一个研究人体如何处理胆固醇的生理学实验室工作。1964年,她在实验室怀了卡玛拉,开始宫缩。在离开之前,她停下来在主管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
“我要分娩了,”戈帕兰·哈里斯后来告诉博士后研究员周玉谦(Yu-Chien Chou)。在医院里,她徒劳地请求允许她在等待分娩的同时回去做实验。
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卡玛拉(Kamala),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先是跟着丈夫去了伊利诺伊州,后来又去了威斯康星州。在那里,丈夫获得了一个终身教职,而她得到了一份较低级别的研究工作。但副总统在她2019年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都很年轻。这是戈帕兰·哈里斯的第一次恋爱。她的女儿写道,这对夫妇“变得像油和水一样”,很快就分开了。
婚姻破裂后,戈帕兰·哈里斯于1969年回到湾区。她选择和她的女儿们在西伯克利的黑人社区定居,那里已经成为黑人家庭的避风港,这一代人离开了种族隔离的南方。
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是伯克利大学的助理生物化学家,他只能租得起一套复式公寓的顶层。金融压力堆积如山。伯克利的黑人朋友们再一次帮助了她。其中一人把她介绍给了她的姨妈雷吉纳·谢尔顿(Regina Shelton),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妇女,经营着一家日托中心。
当他们的母亲工作时,卡玛拉和她的小妹妹玛雅和谢尔顿住在一起。当实验进行到很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过夜。周日早上,谢尔顿带着女儿们去第23大道的上帝教堂,那是一座黑人浸信会教堂。
副总统的儿时好友卡罗尔·波特(Carole Porter)说,戈帕兰·哈里斯一直注重女儿们的印度身份:她带她们去印度,并邀请她们的父母来西伯克利做客。但戈帕兰·哈里斯也想让她的女儿们扎根于她们的黑人身份,并让她们做好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针对她们种族的攻击。
戈帕兰·哈里斯也想让她的女儿们明白,她为什么经常不在家。于是她把他们带到实验室,让他们给试管贴标签。她希望,这些探访可能会帮助女儿们想象自己的生活,她们的生活既以自己的工作为中心,也以自己的家园为中心。
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正在一步一步地朝着她的目标前进,她的目标是破译乳腺癌如此致命的原因。她和合作者已经确定了与雌激素结合的受体,引发生殖系统的变化。后来,她帮助解开了这些受体的功能。
但她的论文未能为她赢得更稳定的学术地位。她在伯克利的导师食言了,没有给她一个教职,而是雇佣了一名英国白人男性。她离开伯克利,去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一家附属医院,在那里她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空间。她想利用她所学到的关于激素受体的知识来建立一幅图片,说明乳腺细胞癌变时发生了什么问题。
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渴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渴望回到旧金山湾区,于是依靠了她所在领域为数不多的有权力的非白人女性之一:著名的乳腺癌生物学家米娜·比塞尔(Mina Bissell),她是从伊朗移民过来的,当时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负责一个部门。
比塞尔聘请了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后者正将注意力转向研究较少的黄体酮受体。
戈帕兰·哈里斯(Gopalan Harris)是一位要求苛刻、有时粗暴的老板,这预示着有关她大女儿管理困难的报道。
但她的强硬也带来了同样多的感情。她称这些学生为她的“孩子”。为了兼顾母亲的身份和论文的截止日期,周曾带着年幼的儿子去教授的公寓,在那里,周写着她的手稿,而教授则和儿子一起玩耍。
渐渐地,戈帕兰·哈里斯自己的病情也越来越重,先是得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后来得了结肠癌。同事们说,在疼痛本应使她无法行走的那一刻过后,她开始工作,甚至正式退休,以腾出工资用于研究需要。
2004年1月,她在给特尔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希望你和我度过一个不那么混乱的新年。”“我太老了,也太聪明了,不能再谈论幸福了!!”-?2024纽约时报公司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时报》。
×
为您推荐:
- 实操教程“微信跑得快免费开挂神器”真实有挂 2025-04-19
- 教程指点“广西友乐麻将有挂吗”分享用挂教程 2025-04-19
-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智能手机导致注意力持续时间变长,但锻炼带来了希望 2025-04-19
- 实操教程“微乐陕西三代控制器”确实是有挂 2025-04-19
- 莫迪总理公布了1285亿卢比的卫生部门项目 2025-04-19
- 游轮入港季节 2025-04-19